福建省唯一关押女犯的监狱,以女警为主,40年改造数万女性罪犯
福建有个村子,叫桐南,早些年你要找还真得绕几条国道。现在导航一搜倒挺好找,只是除了土路、田埂、高楼和小商店,这里还有一座三百亩大的女子监狱。说起“监狱”,多数人脑袋里就蹦出灰色高墙、冷清铁门,其实再往里面走,你能闻到桂花和饭菜的混合味,也能看到十来个巡逻的女警和成百上千的女人,从各自的命运扯进这片福州“飞地”。

这监狱,说起来也折腾。1985年刚建那会儿在南屿镇,后来地皮不够用、人多了,台灯下的“女民警”们还得抽空搬监区、拎箱子。九二年,他们搬过一次家,住进省城连江中路的小门脸快连,看着人来人往的主道,心里还是觉得局促。等到2013年冬天,夜里下着薄雨,警灯排成长龙,一千警力把三千多个女犯分梯队转移回南屿新址。你想啊,这事儿可不是一般的大搬家,比学校开学还壮观。
其实这地方不光“关人”,生活痕迹也挺重。早上六点,炊事班涨火做饭,医院里护士推着轮椅,分监区的女警送货备品像赶大集。十二个科室,医院、供应站、文化分区全有,甚至电视、互联网信号都能接得到。这几年说是严格管理,可进了院子,树影婆娑,偶尔能听到民警在档案室聊天,谁家孩子又上了好大学。你要是问这些女警她们的感受,多半也不会跟你煽情,大抵一句:咱们是干正事儿,家里也得照管。
那些“五十后”“六十后”,最早一批进来时还是红旗下的姑娘。穿警服觉得新鲜,提案子也爱插两句生活琐事,说起来都像是老邻居。几十年一点点熬出来的底子,才让监狱每年评先进,也让“女监人”这个词越发硬气。其实你去食堂边上“溜达”,说不定正赶上谁在教新来的民警如何填表、如何劝导落魄女人别自暴自弃。听着这些老民警的碎话快连,就像在冬夜灶头边煮汤,热气腾腾。
而那些七十后,扛过风雨,见惯了体制的更迭。她们也是会破涕为笑的中年人,家里有老人要供,有孩子。平常工作极细――管安全、治病、帮家属递话,忙得不着家。其实不光有铁面无私的一面,她们也是“最美家庭”里的主角,下班开电动车去送货,回家还得给爹妈熬粥。你在监区听她们说话,也许一句不经意的嘱托就是“姑娘,路灯坏了记得找维修”。

等到八零后,贴上“自我”“叛逆”标签进了警营,才发现,这高墙内要求的不是棱角分明,而是能吃苦、懂倾听的耐心。她们学姐就是前一天还陪犯人熬夜做心理辅导,第二天早晨抽空带孩子去医院。大事小事一把抓,早已从青涩变成熟。她们要会审讯,也要懂得扮演文化老师,有时候一堂课下来,光是劝走两个哭鼻子的服刑人,还得跟狱友解释“什么叫顺心做人”。闲下来的时候,也能在运动场溜一圈,回家发条朋友圈:今天又教会老王写了自己的名字。
九十后,脸上有稚气,刚进来时“爱美爱玩”,其实也能在高墙下做点不寻常的事。舞蹈排练、志愿服务,没了谁喊累;不用说,每月还要给服刑人员做心理讲座,跟姐姐学习怎么分辨谁撒了谎。穿上警服一板一眼,脱下警服又敢折腾,有的大晚上带警犬巡逻,有的下班跑去帮忙煲汤,里外都是“生机勃勃”的光景。这些人,能苦能甜,谁说年轻人靠不住?

其实监狱里的服刑人员,每年“开学第一课”也很有讲究。不是正规学校的铃声,却有生命教育、法律意识、技术培训快连,全都得上。有人一进来愣是连字都不会写,几年下来能背书、做题,甚至考了全国自学考试的文凭,洗净过去,盼着有天能堂堂正正地回家。有时候课后还能听到几个女孩念叨:“今年自考过了,下一步就是学点手艺,回去了也有用”。
当年熊某进来的时候,大女儿才十岁,小的还在吃奶。她拐卖儿童,害了别人家的团圆,报应来得也快。丈夫的意外、孩子的远离,八年没见过各自,她在亲情拓展见面会上,隔着一道栏杆试着辨认哪个是自己的骨肉。孩子上台,熊某只能靠年龄和穿着猜,看到一家三口抱在一起,她哭得缩成一团:“我已经不认识他们了”。这话说出来,连带值班的女警都有点鼻酸。讽刺在人间轮回,多少人付出代价都来不及后悔。

陈英是另一种命运。她当年嫁给了青梅竹马,婚姻生活算是顺遂。谁曾想摊上了生意伙伴,不慎帮人融资,双双获罪。进了监狱,家里变天,智障儿子得靠七旬老母照看。锒铛入狱后第一次见丈夫,眼泪流得止都止不住。平日里为家担忧,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。幸亏分监区长和管教民警总去谈话,帮她一点点拾回改造信心。陈英感叹:如果没有这些人,我可能早倒了。
你要问这些女民警对生活是什么态度,多半也是一笑了之:再苦也得熬,再难照样把日子捡起来。她们能顶半边天,又懂照顾小家。送货、查岗、做活动,谁家老人有事,姐妹们自发去探望。改造工作里,亲情帮教尤其重要,有时一场见面会,就能让几个服刑人服软、开始认真生活。几年办下来,超过六千人受益。有时候志愿者来捎个信,服刑人当场红了眼;有的家属说“等你回家”,一句顶天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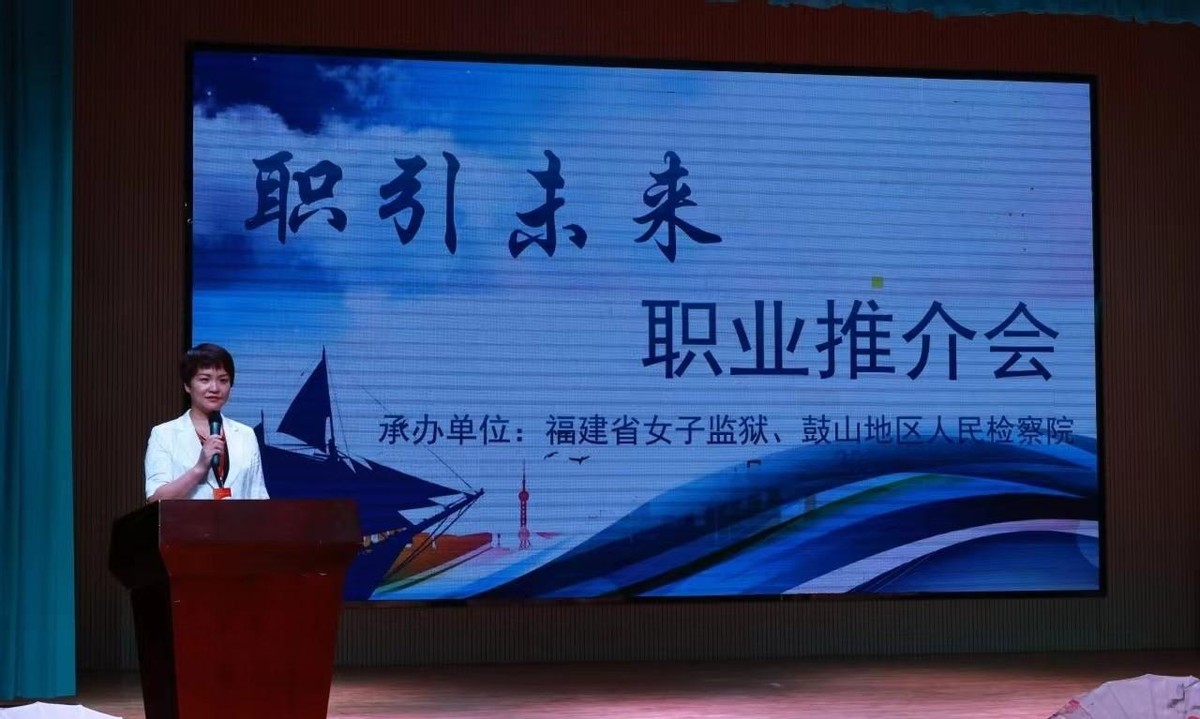
说监狱像学校,像医院,像大家庭,其实更像一面复杂的镜子。高墙之中藏着伤痕,也有希望。女警、服刑人,每个人都在为生活找出口。有人悔过,有人成长,有人等待,更多的只是数年悠悠时光里,那个还没说出口的“下一站会怎样”。
也许哪一天,桐南村的秋风里,又有新的人走进这道门。她们会不会也像前人一样,在平凡和苦难中,把日子细水长流地活下去?留一点想象,给“后来的我们”。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