晚清有个女子监狱,里面有个“逍遥自在床”,让女犯人受尽折磨
道里监狱:一个女人命运的地狱

你说,人这一辈子,有多少事是自己选的?换个地方,换个名字,命运就真能重来吗?道里监狱的故事,就是这样令人堵得慌——要是生在别处,也许只是一介平凡女子,可偏生赶上那个年月,那座城,还有那些异国掌权人的阴鸷嘴脸,命就变了味,一脚踏近地狱。
哈尔滨,光绪二十七年,不是每个人道里的夜晚都能睡个囫囵觉。俄国人把监狱修得又高又厚,统统只收女人,五湖四海的,大多是清朝女子,还有几个说着日本话、朝鲜话的,有的脸干巴巴,有的眼睛湿得像刚打过雨。关进去那一刻,有的人还在不服气地嚷,有些像是终于认了命,跌进黑暗。不过谁都撑不住太久。这里有种刑罚叫逍遥自在床,听名字像是要给盼头,实际上呀,是地狱路上的一张“鬼床”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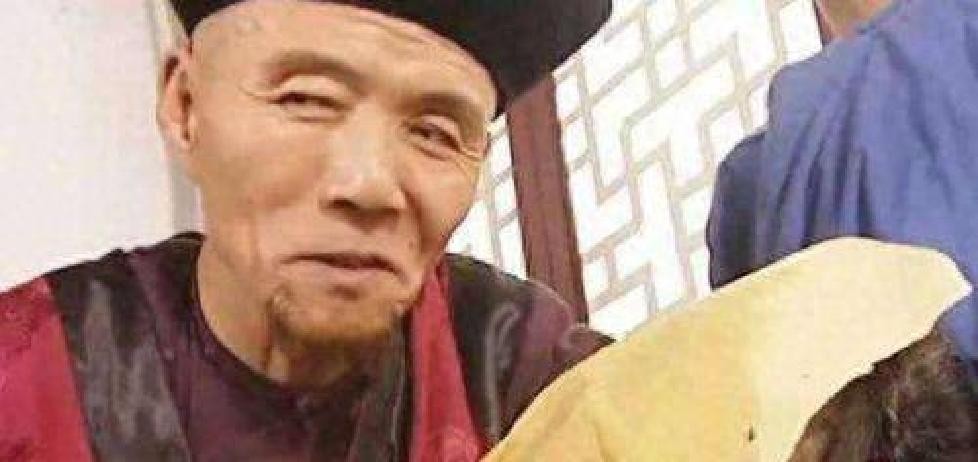
逍遥自在床可不是啥软塌塌棉被窝。四根粗绳,横在房梁上头,像蜘蛛结网。女人被五花大绑,拎在半空里,脚离地,地板上的灰竟像离她好远的另一个世界。最开始是沙俄守卫发明的,他们冷冷盯着你,像在考察牲口的耐力。悬着的身子,不管多硬气,骨头都开始尖叫般地疼,麻木还未及时救急,就被另一种难以说清的羞辱侵袭。
有人问,痛可以忍,丢了隐私怎么办?一屋都是女人,可人心隔肚皮。还有守卫那双冰凉的眼,以及挂在嘴角的那点恶趣味。羞耻感一波波地卷上来,愤怒、委屈,还有那种觉得自己已经不是“人”的绝望,全堆在心头,只能在黑暗里咬牙,巴望早点结束——天知道,这样的“自在”,能撑几刻钟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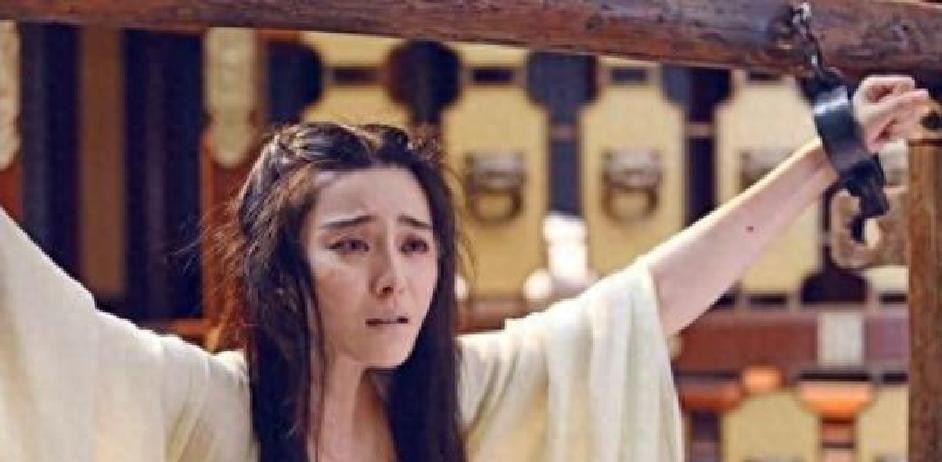
时间一久,监狱里的人换来换去。沙俄走了,清廷衙门的人来了,后来日本人也把道里接了过去。刑罚呢?省去了繁琐的纸面更替,还是那一套折磨人的门道。倒霉的是,每次政权轮替,总有人想试试这些“老规矩”。有一年,竟有几个俄国人栽进去尝了“逍遥自在床”快连,旁观的女人脸上都挂着奇异的表情,不知是幸灾乐祸还是旧恨难消。可谁又能为自己讨回公道呢?那些天以后的女人们,进出监房,脚步轻得像怕惊醒窗台上的鬼魂。
讲起这些事,幸存下来的老人总要咳一咳,嘴唇贴着瓷碗叨念一阵。有人说,沙俄人用夹棍,有人记得辣椒水流进眼窝痛得人嚎叫。蜻蜓点水、老虎凳、贴加官……数得过来,受得过吗?道里的空气里,连铁链都敲出了女人的叹息。那种苦,连啃铁锁的小老鼠都不愿接近。

活在道里,外面的人怎么想,其实不太重要了。有人曾试着偷递两句话进来,纸条上写着家里的新米刚蒸熟,有人刚添了孙儿。可监房里头,眨眼间就像被人泼了冷水。老婆婆念左手的小指,年轻点的姑娘咬着嘴唇——不是不想家,不是不想逃,只是,挣不开的东西太多了,绳子是死的,人心也是死的。
偶尔也有人疯了。那种疯,不是嘶吼,不是絮叨,而是当天还在哭,第二天突然安静下来,好像把心收拾进了小箱子。她不肯多说,别人问她死了吗,她就摇头:“不是死,是不想让别人看见我还在痛。”总有某些夜晚,巡逻的守卫走开了,女犯们之间互相贴靠着,只为在身体的热气里找一点残余的人味——你要说高墙之内没有女人之间的小温情,也许真的太绝对了。可温情,有时没能抵住恐惧。

那些年道里监狱成了女人的牢笼。每座铁门都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关卡,每根绳索都是命运的脚镣。后来听说日本人有时也把几个俄国人套上床子试试,算是为旧账找些滋味吧。不过,那铁门背后快连,终于没人再细数过多少女人从悬空的绳索上昏死,多少人在羞辱下选择放弃讲话。道里监狱变成了传奇,也变成了诅咒,只要有人提起哈尔滨旧城,就总能听见一两个关于女人如何在“床上”死过一次又一次的故事。
我有时候想,如果那些女人没有进这座监狱快连,会是什么样子?是不是有人本该靠着巷口的老井洗衣服,有人本该在三道街教孩子识字。她们有家,有名字,有不会被摧残的世界。可命运选中了她们,卷进一场大国混战,卷进了沙俄、清廷、日本人的黑箱子。谁又能帮她们选更好的剧本呢?

后来世道变了——再也没听过哈尔滨那角落里有人用“逍遥”来形容绳床了。倒是老人们偶尔在小院里提起那监狱,说得轻描淡写,像是在讲旁人故事。可是每个字里,都是旧伤痕的余温,总让人觉得,这样的苦,不该只留在过去。世上女人太多,还能有多少把命握在自己手里?
那些苦难、羞辱、无力,也许没有谁能同她们共情到底。只有那条逍遥自在床,在历史某个阴影里,悄悄吊着很多女人的名字。我们讲这些,不是为了渲染血腥,而是想问一声:权力和制度替谁撑伞?又有多少人,有过机会避开那个地狱?
风吹过旧城墙,几声叹息随风而去。剩下的,就让时间慢慢磨薄吧——只希望今天的人,再别被套上那种无法落地的绳索了。





